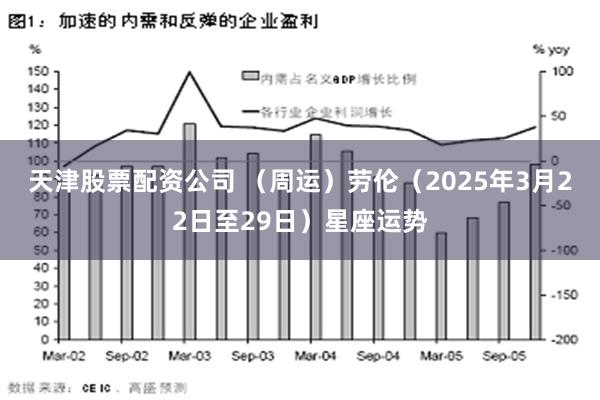安藤忠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称是“游击队员”,这在古往今来的建筑师里独一份。
卡尔·施米特——20世纪最伟大也最富争议的思想家之一——曾在他的名作《游击队理论》里,为游击队下过一个“暂时”的定义,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定义的适用性极好。定义包含四个要素:
1.非正规性
2.高度灵活性
3.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4.依托土地的品格
以“游击队员”身份登上建筑舞台的安藤忠雄,在这四点上,同样非常符合定义。这种符合性尽管在其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建筑生涯中有各种动摇,但总的来说,直到今天,依然在最重要的一些支点上被顽强地坚守着,尤其是绵延20年依然在“有机发展”中的直岛系列项目。

“战士”≠“游击队员”
你可能没机会亲身去直岛参观,但各种与安藤有关的建筑图册都会有详细的图文介绍,比如我手头这本厚达1000多页的大画册《安藤忠雄全建筑1970-2012》。不过如书名所示,它出版相对较早,最近十年的新作无法收入,可能补上2020年出版的《建筑家安藤忠雄》和去年出版的《安藤忠雄与光影同在》,会对他的最新思路与作品了解更深入一些。
当然如果正好有安藤的建筑展,这种了解又会增添强烈的直观性,比如9月刚刚在上海嘉源海美术馆(这座美术馆是安藤在中国建成的最新作品)落幕的“安藤忠雄建筑:对话”大展。而我对直岛项目的诸多直观感受,同样来自一个大展——三年前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举办的“安藤忠雄:挑战”展。
当时,艺术中心的三楼围出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布置成直岛诸项目的单独展厅。右侧墙上是各个单体建筑的简介和图纸、视频,左侧墙上则是在已建成的项目中展示的诸多艺术作品图像,而中间整个宽阔的场地,被直岛的模型所占据。与一般的建筑模型用材完全不同,这个“直岛”是用刨下的木屑直接堆出来的,极具“有机感”。那一个个项目,就散布在——或者不如说埋在——这堆巨大的木屑之间,看上去就像是散落的地堡、地窖甚至地沟,当然,只是看上去,实际上它们被埋在地下的空间是如此丰富,迂回曲折、彼此映射,似乎每一寸光与影的呈现,其效果都被仔细琢磨过。这一设计思路,在我看来依然极忠实地秉承了安藤最源初的“游击队”原则,而与他眼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遍地开花的各“地标”项目(此类项目已达20个左右)形成鲜明的对比。
安藤的“老奸巨猾”——自十多年前做过他的专访之后,他在回答各种刁钻问题时的狡猾和游刃有余,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种对比中显露无遗。他如今已经非常清楚该在何时何地坚持自己的内在品格,而在另一些对他来说比较不那么重要的地方,向资本力量妥协,先把钱挣了再说。

在回复我相当直白的提问“现在的你,还是不是一名老‘游击队员’”时,他答非所问:“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名‘战士’……‘游击队员’事实上就是在不同城市做项目的‘战士’。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做不同的项目,就是不同的战场,无论在哪个战场,我都是一名‘战士’。”
然而仔细想来,“战士”和“游击队员”,并不是一回事。游击队员固然在宽泛的意义上也是“战士”,但它有着自己更为独特的内涵。相比之下,安藤如今赋予“战士”一词的含义,恐怕更多属于(因他的功成名就而转变成为的)正规军,而非游击队。正规军正如地标建筑,必须穿上鲜亮的、雄赳赳的制服,浑身佩满领章、肩章、勋章。在施米特看来:“军装就表现了正规性,其正规性远甚于职业服装,因为它展示了对公共性的控制;随军服亮出来的还有公开展示给人看的武器。”而相反,“游击队员恰恰避免公开携带武器,在隐蔽处作战……更经常穿任何一种便服作掩护。隐秘和黑夜是游击队员最强大的武器,他不可能老老实实放弃这两件武器,否则会丧失非正规性这一活动空间,从而将不再是游击队员。”安藤在为自己辩解时,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两者。并且类似的话对别人说得多了,连他自己也信了吧。
不过,作为从一开始就非科班出身的“野生建筑师”,安藤骨子里的“游击性”,也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彻底驯服。他的真正最有创造力的部分,始终与这种游击性相伴随,而在各个时期,在各种与资本、与政治、与环境的缠斗中涌现出来。
游击队与空间
安藤的早期履历表上,开门见山写着:“公元1941年生于大阪,以自学的方式学建筑,1969年设立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
这本身就是一桩奇事,因为今天你很难想象高度专业化的建筑设计可以“自学”,那只能是极度动荡而激越的1960年代发生的事情。那也正是火热的属于游击队的年代。
1965年,安藤实现了一趟旅费60万日元、长达7个月的周游世界之旅,途经苏联、芬兰、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南非、马达加斯加、印度和菲律宾。这是彻底游荡式的自学之旅,显然也是他“游击”的起点。在他上路前两年,卡尔·施米特以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等人的新型游击战实践为背景,写出了《游击战理论》。旅行结束两年后,切·格瓦拉战死,旋即成为全球青年头号偶像。第三年,二次欧洲之旅途中的安藤亲历了法国“五月风暴”,甚至亲身参与了挖路筑街垒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安保斗争”如火如荼。这种激昂的时代情绪一直伴随着安藤的建筑“自学”,直到1970年11月,“三岛由纪夫切腹自尽,似乎正象征了‘创造年代’的终结”。
其实要说60年代的“终结”,相比三岛这个右翼分子带来的冲击,另一桩让全日本震惊的事件恐怕影响更大,而且与游击队直接相关,那就是1972年2月的“浅间山庄事件”——联合赤军劫持人质与军警对抗整整十天,并经电视现场直播,成为日本战后勃兴的左翼运动的转折点,自此以后社会风向完全倒转。而正是这一年,安藤在《都市住家》杂志上发表了“都市游击队住宅”,公然宣称要把人们的住宅打造成“都市游击队基地”:“如同在都市中忍辱负重的游击队,采取一切手段动摇既成的价值体系,使建筑作为都市的异质元素,在各类场合都具有爆发性的力量……”
在左翼社会运动遭受巨大挫折、“人心思定”那样一个关键时刻,安藤却逆风而上,把乌托邦社会理想,内化到他的建筑事业中。

所谓“都市游击队住宅”,具体来说,就是包含在这一名称下的三个住宅项目,都采用自我封闭的结构,在四周筑起高墙,形成一个完全将资本主义都市排除在外的空间。用安藤自己的话来说,“都市游击队住宅是宛如洞窟的住家”——由此可以看到他一直绵延不绝直至直岛项目的“洞窟”思维的起源。而恰恰因为其封闭性、隐秘性,为了让人能住得不过分憋闷,安藤在这些项目里充分发挥日本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反而将内部空间做出各种曲折变化,“为狭窄的住家创造出无限的小宇宙”。比如逼仄的“住吉长屋”(1976年),其架空在狭长中庭上方、连接两侧小楼的那条露天过道,就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小兵张嘎》里,武工队员在一座座平房的屋顶和墙头上游走自如的长镜头。
的确,游击队需要,也必定会为自己塑造出一种独特的空间。正是这种空间感,与安藤心目中的建筑空间产生了共鸣。施米特如此表述这一空间:
“游击战中出现了一个结构复杂的新的行动空间,因为游击队员并非出现在公开战场上,并非在公开的前线战争中的同一层面战斗。游击队员将自己的敌人逼到一个空间,从而给传统的正规战场平面加进了另一更难以捉摸的空间——将炫示的军服置于死地的纵深空间。游击队员以这种方式在陆地领域提供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并未因此减弱其效应的与潜艇的类比,后者同样给旧式海战赖以展开的海洋表面添加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深层空间。游击队员从地下出来扰乱公开舞台上展开的常规正规军的战术行动层面,也改变了正规军的战略行动层面。只要充分利用地形,相对较小的游击队便可钳制大量正规军。”
不用再进一步细化游击空间与建筑空间之间的类比,只需从施米特的表述中提取一些关键词——结构复杂、难以捉摸、纵深、深层、地下、充分利用地形、相对较小——几乎就能涵盖安藤1970~1990年间大多数作品的特性了。无论是七八十年代大批量的小型私宅项目(富岛宅、住吉长屋、小筱宅、城户崎宅等等),还是佐用、冈本、六甲等相对大型的集合住宅,又或者是大阪中之岛项目、AKKA画廊、东京涩谷方案、京都TIME'S商场等公共空间,均是彻底依循地形(尤其是山坡与河流),尽可能将通常用以塑造外形的“立面”缩减至最不起眼的程度,而将必需的空间向地下延伸,构造出错综复杂的内部结构;可以说,这些作品完全体现了施米特游击队定义中的“依托土地的品格”“非正规性”和“高度灵活性”,至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我想对在那样一个转折时代逆潮流而动的安藤,都不必专门提及。
转型:阿波罗之光
1980年代末,安藤迎来了转型。内在原因,可能是任何建筑师都会有设计更重大、更具“永恒性”的项目的冲动;外部原因,则是随着他的成功之作渐多、名声渐起,委托项目的数量、类型、体量都在增长。当然这会与最初突出“隐匿”的游击队理念有所矛盾。安藤赖以协调这一矛盾,并得以成功转型的最重要的“武器”,是光,或者说,阿波罗。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区分了希腊艺术的两种倾向: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或曰酒神与日神。其中,阿波罗是造型艺术的象征,因为形体和色彩都必须靠光来显现;如果没有光,那么一切都隐没在黑暗中——狄奥尼索斯式的迷醉之夜,那是音乐的象征。
早期安藤,身处以游击队员身份向社会和都市挑衅的激情之中,以“消失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异质性和爆发力为特征,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他的狄奥尼索斯阶段。1980年代末,非常有意味地,以一系列宗教建筑为媒介,他完成了转身,或许正因为——上帝说,要有光……

当然,安藤对建筑中光线的作用一向都很重视,在那些逼仄、隐蔽而幽深的“游击队式”建筑中,光几乎是仅有的可以用来调节内部气氛不至于压抑的元素。这方面对安藤影响最大的,是勒·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
“我通过朗香教堂,从勒·柯布西耶那里学到的并不是‘形’的手法,而是只用光也能实现建筑的可能性……当你走进朗香教堂的内部空间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与外界隔离的黑暗,但给你印象最深的是透过窗户、墙壁上地缝般的缝隙照射进来的多样的光线……这样巧妙的设计使我有了对空间进行了解和分析的冲动,但最终我还是沉迷于那梦幻般的光线洪流中不可自拔。”
柯布西耶的这一影响是终身的、极深刻的,因为你在今天的直岛诸项目中,同样可以沉浸于这种近乎封闭的空间里的光影的游动与嬉戏。著名艺术史家菲利普·朱迪狄欧为自己研究安藤的专著取名《安藤忠雄与光影同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但是光毕竟更可以用以显现和塑造外形,转型中的安藤逐渐加大了对建筑外形的关注。整个转型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他对光的外部造型功能和内部戏剧性功能之配比的不断调试。
地标时代:妥协与坚守
19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的安藤,似乎一直处于这种阿波罗式显形与游击队式隐匿的拉锯与调和试验中。有时候项目地标性更强一些,外在造型就占上风;而如果没有太强的地标性要求,又有足够的自由度,比如大阪府立近飞鸟博物馆、真驹内泷野陵园头大佛以及直岛系列等项目,他很自然又会聆听“内心的声音”,把自己重新埋进“风土”里。
但是随着声誉日隆,接到的地标项目显然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国近十来年集中刮起了一股“安藤风”,而这些作品,在我看来有相当一部分,只是将早期成功作品中的元素,稍稍结合一些当地风土人情之后,进行某种“地标化变异”的结果。这样当然比较省力。
比如上海保利大剧院,就是这样一个勉力将安藤式“元素”融合进一个巨大的箱形地标建筑的典型。实际上,如果你俯瞰它,会发现类似直岛地中美术馆的数个几何形“坑洞”,只不过美术馆的那些洞口背后是纵横交错的箱体,而保利剧院的洞口连接的则是一些“圆筒”。然而在直岛,这些坑洞通向的建筑主体完全被埋于地下——它们是被掩蔽的“战斗工事”的出口。但地标建筑当然不能允许自己“看不见”,相反越吸睛越好,那些在直岛浑然天成的“大地洞窟”,于是变异成了“在大箱子上挖洞”……

曾经的“游击队员”倾心于反抗,对各种既定的秩序、制度、成规和意识形态都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那时的安藤可以完全不顾业主的舒适度而设计自己认为有创造性的住宅,也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根本意图将项目扩大、预算超支,屡战屡败痴心不改。而如今,这位八旬老“战士”虽然斗志不减,依然高呼着“挑战”的口号,对于挑战什么、如何挑战,却显然有了精明的计算/算计。
施米特指出:“从长远观点看,非正规必须借助正规来正当化;因此,游击队员面临两种可能性:得到既存正规者承认,或者靠自己的力量奋力获取新的正规地位。这是艰难的抉择。”但无论如何抉择,游击队本身都将“在技术-功能主义过程的顺利发展进程当中自动消失,有如一条狗从高速公路上消失”。
而已经进入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安藤,大概已经将最好的结果握在手中:既被既存正规者承认,又靠自己的力量夺得了新的正规地位。但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游击队员”与“一代宗师”之间的张力并不会就此消失——只要他还想“创造”。

《安藤忠雄与光影同在》
[美]菲利普·朱迪狄欧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7月版

为解答这些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基金报在《布局核心资产 拥抱指数投资新时代——中证A500指数投资论坛》上,邀请到富国基金量化投资部ETF投资总监、中证A500ETF富国基金经理王乐乐,他以《从“表征级指数”到“投资级指数”——宽基演化新篇章》为主题,深入解读中证A500指数的演化和迭代。
《中国基金报》对本平台所刊载的原创内容享有著作权,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建筑家安藤忠雄》
[日]安藤忠雄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5月版

《安藤忠雄全建筑1970-2012》
马卫东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
举报 文章作者
割麦子
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相关阅读 日本东京涩谷一建筑发生火灾 或有人员被困日本东京涩谷一建筑发生火灾 或有人员被困
0 11-17 19:37 中国建筑行业信息化投入占比不到0.1%,法国软件巨头来华成立合资公司达索系统与中南建筑设计院的合资公司,将成为“达洛兹时代”的首个关键项目,此次的项目瞄准的是中国城市与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266 11-01 21:57 中信建投:A股建筑央企投资性价比提升,静待利好政策落地中信建投:A股建筑央企投资性价比提升,静待利好政策落地
0 10-07 17:02 上海:鼓励有意愿的居民利用存量居住建筑屋顶建设户用光伏,推进实施多产权存量居住建筑光伏试点上海:鼓励有意愿的居民利用存量居住建筑屋顶建设户用光伏,推进实施多产权存量居住建筑光伏试点
19 09-13 17:55 华蓝集团:目前建筑修缮相关业务占公司总营收比例较小互联网证劵融资华蓝集团:目前建筑修缮相关业务占公司总营收比例较小
0 08-27 16:18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